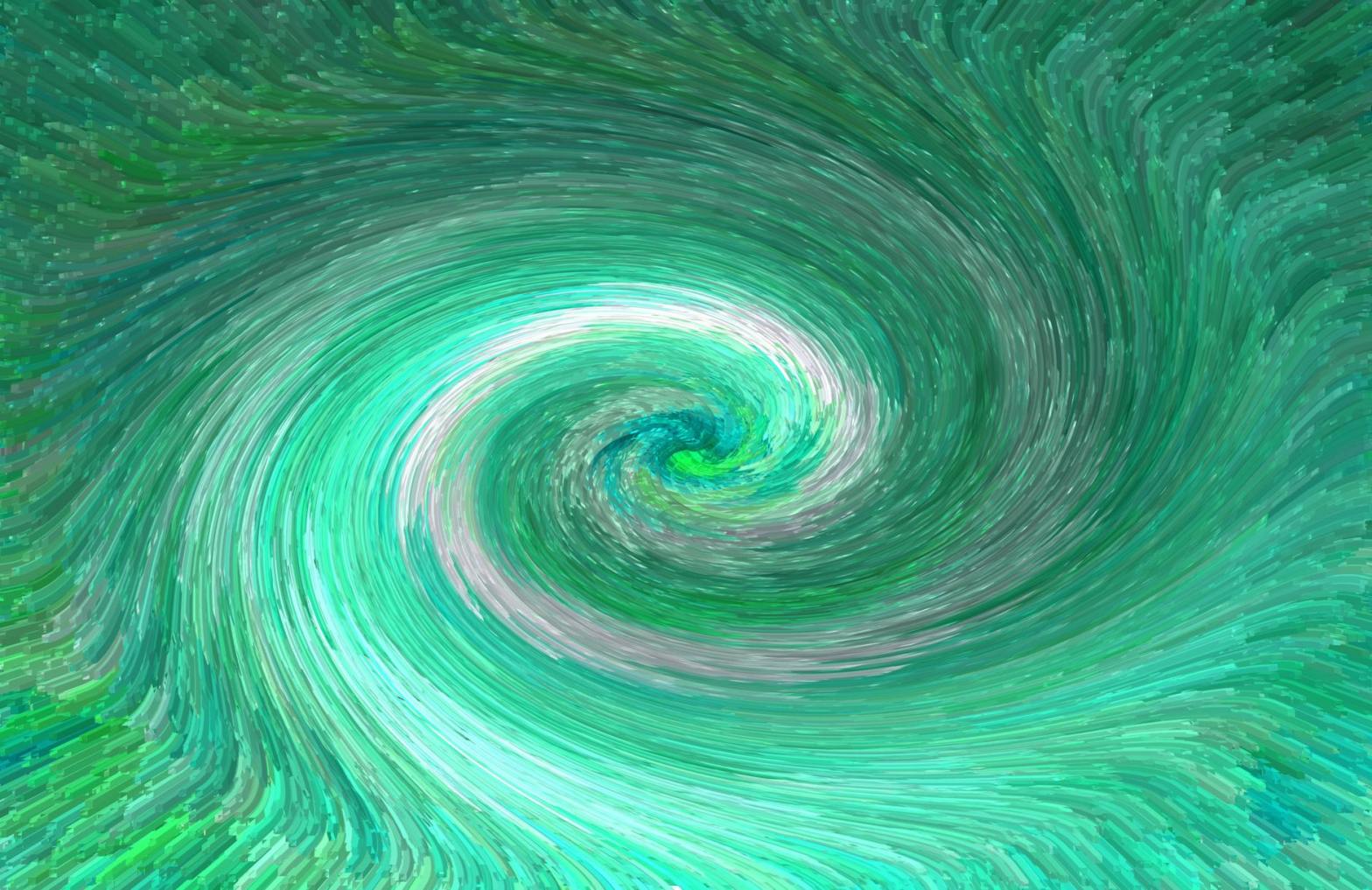第一節 第三次出行
李融湘第三次懷孕,是在一個再平凡不過的午後。
她把報告放在餐桌上,語氣平穩,沒有期待,也沒有遲疑。何長聲看了一眼,點了點頭,甚至露出一點笑意。他已經習慣生命在家中出現,也習慣自己扮演那個穩定的角色。
那是一個女兒。
產後一個月後,她回到家。
她把行李整齊地放在客廳一角,衣物分門別類,證件、文件一疊一疊收好,像是早就演練過無數次。
她說的第一句話,不是告別。
而是:「我們先把離婚辦好。」
何長聲一時沒有反應。
他站在原地,看著那幾個箱子,腦中浮現的不是爭吵,也不是質問,而是一種荒謬的錯位感——彷彿有人突然把錄音帶倒轉,而他還來不及調整速度。
「妳說什麼?」他問。
她沒有重複,只是把話說得更完整。
九年的真相
「我婚前,就有一個日本男朋友。」
她說這句話時,語氣沒有歉意,也沒有防衛,像是在陳述一段與情緒無關的事實。
「我們相愛,但日本物價太高,他無法成家。我也不想讓你覺得我是為了錢才結婚。」
她停了一下,像是在確認每一個詞是否準確。
「這九年來,我從你這裡,已經有足夠的資源,在九州大阪郊區買地。他還在等我。」
何長聲沒有坐下。
他的腦袋像被人敲開,卻沒有聲音跑出來。所有過去的畫面開始重組——她產後的消失、那些「先離開人間」的時刻、她對家庭永遠保持的那一點距離。
原來不是病。
是分心。
「我希望你成全。」她最後說。
那不是請求。
是結算。
理解的崩塌
那一刻,他忽然什麼都明白了。
明白她為何在最需要被依賴的時候選擇離開,明白她為何始終站在家庭的邊緣,也明白她為何能如此冷靜地安排每一次「出行」。
理解,沒有帶來釋懷。
只帶來徹底的崩塌。
他沒有罵她,也沒有挽留。
他只是問了一句:「孩子呢?」
「三個女兒,跟你。」她說得很快。
那一瞬間,他忽然覺得自己像被抽空。
不是被背叛。
而是被掏空。
第二節 結紮
離婚手續很快。
沒有新聞,沒有風聲。條通的夜仍然熱鬧,錄音室照常運轉。只有家裡,安靜得不像人住的地方。
孩子們還小,不懂發生了什麼。
她離開後不久,他做了一個決定。
結紮手術。
不是報復,也不是自責。
而是一種封存。
他知道自己不再適合把任何人帶進「家」這個概念裡。他已經把十年最正常的人生——成家、生子、期待——全部用完。
夫妻一場,到此為止。
揮別正常生活
那一年之後,何長聲的人生軌道,徹底偏移。
他仍然是條通皇帝。
只是那個稱號,開始變得有名無實。
他不再準時回家,不再計算作息,不再為了明天留力。夜生活重新佔據他,應酬、酒局、女人、笑聲,一切都來得輕,也去得快。
錢仍然進來。
更多,甚至更快。
但他已經不在乎累積,只在乎消耗。
揮霍,成了一種生活方式。
不是因為快樂,而是因為不想停下來。

正式登基
條通的人,很快發現他的改變。
過去的何長聲,精準、節制、掌控節奏;現在的他,豪氣、任性、不留退路。他開始被真正稱為「皇帝」——不是因為權力,而是因為距離。
他站在最亮的地方,卻沒有人真正靠近。
那是一種正式登基的孤獨。
裂音
夜深時,他偶爾會想起父親何勿棄。
那個一生壓抑、內斂、始終把情感放在事業後面的男人。當年他以為自己不會走上那條路,卻在這一刻發現——只是方式不同。
父親選擇沉默。
他選擇喧囂。
但核心,都是一樣的失聲。
三個女兒在家中長大。
他負責供養,負責安排,卻不再試圖補回完整。他知道,有些裂縫,不是靠陪伴就能填平。
李融湘的人生,從此不再出現在他的時間線裡。
沒有祝福,也沒有詛咒。
只是切割。
第三節 條通之夢
夢裡,他常回到條通。
不是最繁華的夜,而是清晨,霓虹未熄,街道空蕩。那些曾經屬於他的聲音——歌聲、笑聲、掌聲——都變得模糊。
只剩下回音。
他站在街中央,忽然明白——
自己真正失去的,從來不是她。
而是那個曾經相信「正常生活」能夠長久的自己。(以下空白)